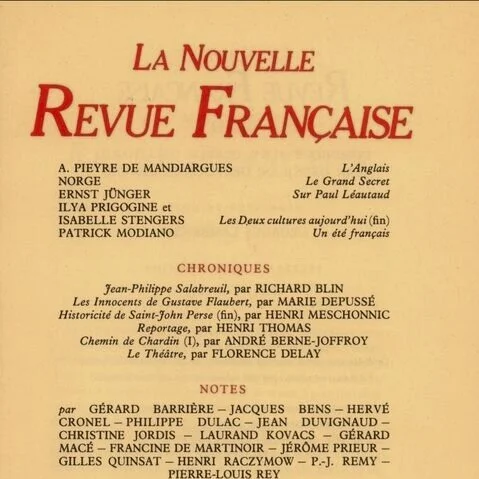即便是以解剖的方法剖開死者的器官,他們也不可能復具生命力。因此死亡被表現為神秘而殘酷的,反過來說,生命力才是一切行動狀態的存在之本,在此「解剖學」本身則可說是被解剖得毫無貢獻了。
eL詩集《失去論》
文/勞緯洛
讀著馬來西亞詩人eL此薄薄的一本詩集《失去論》,確實能感受到他詩中獨特的聲音,帶著一種讓人易於進入的魅力:特別難得的,是他從不用生澀朦朧的抒情詩路數來製造意境,往往以簡練的文字勾勒其背後更深層的哲思,讀畢卻又在片刻間難言所悟。此種知性與曖昧主客擁抱的詩意,許若:「風把網撩了撩。/網把風搓了搓。」(〈可有可無〉)
eL首先是作為一個滿帶挑釁的「詞的解剖者」現身在他的詩裡。他所解剖的詞的主題由日常入手,像理髮、童謠、流行曲、食物、動物、植物、自然元素等無不涵蓋,乃至較為嚴肅的命題,比如詩、革命、時間、自殺或死亡本身,在他筆下俱變得具體,裂成一塊一塊,失去了既定的形態與中心。尤其〈解剖學的貢獻〉,作為整本詩集的卷首之作,當為eL詩的典型。先錄如下:
他們把死者的心剖開
卻不能使他更開心。
他們把死者的胃剖開
卻不能使他更開胃。
他們把死者的眼睛剖開
卻不能使他更大開眼界。
活著的人剖不開死亡。
死亡真的那麼頑強、可怕了
嗎?
然而此時此刻
它竟一點也不能把死者
嚇醒。
在解剖學與死亡的主題下,eL把握到「開心」、「開胃」、「大開眼界」等慣用詞的共通結構(即「開」配以人體器官),並進一步找出這些詞語狀態背後的驅動力,正正便是生命力。只是,當人死去後(即失去生命力),他還能「開心」、「開胃」、「大開眼界」嗎?不,即便是以解剖的方法剖開死者的器官,他們也不可能復具生命力。因此死亡被表現為神秘而殘酷的,反過來說,生命力才是一切行動狀態的存在之本,在此「解剖學」本身則可說是被解剖得毫無貢獻了。事實上,對既定主題進行解剖,並將其支離破碎地如實呈現,當是eL的熟手技倆,亦可謂整部詩集之本色當行。
這種詞的解剖技藝,往往更針對於活化以至解放語義,像鴻鴻的序〈文字遊戲與價值信仰〉點出《失去論》中的這些「說理詩」的特點,正是「對既有的命名,提出質疑或抗議。」eL作為馬來西亞詩人,在此當亦可理解為遊走在邊緣位置的異聲,在主流習用華語話而言,他便要對話語霸權作出逆反,矢志「拿回自己的語言……甚至有種跡近偏執的挑釁。」〈火的清白〉可充一例。在詩中,詩人首先一臉嚴肅地朗讀不同報章對「火燒掉了木屋。」一句的說法,比如「祝融光顧木屋」、「火魔沒收木屋」等,都是我們或已慣用的修辭標題。然後,詩人卻像以忍俊不禁的口脗(也令讀者忍俊不禁),開始提出「大火」與「小火」本質的差別、「祝融」與「火魔」帶來的詩意或聯想有何意義、火會否真懂得「吞噬」木屋……小結以一句語氣挑釁的反問:「難道事實不是,僅僅火/燒掉了木屋,而已?」接著便開始慣有的質疑與諷刺,說人類擁有「遣詞用字的高深功力」、「美妙豐富的想像力」,然而「火甚至不知道這動作就是所謂的/「燒」!」他如此驚醒讀者,繼而詰問:「人類難道不該為文字/負上更多的責任?」eL在此呼告我們這些每天大量使用文字的人(尤其以言為寺的詩人),應負上為文字更新活化的責任,免得因我們的慣常習用而使那些詞語陳腐近亡。即便如為人熟知的〈花的語言學〉中,「我曾經玫瑰了你,彼時春日綿綿/你卻曇花了我。心緒一時棉花不已」之句亦見此路詩法,可謂全都表現著eL對於解放文字與語言的理想:「讓字都被收割了吧/我們的荒蕪就會顯得一片/欣欣向榮。」〈劃掉劃掉劃掉〉
除了對詞的解剖與挑釁,我發現eL的《失去論》事實上更內含一種謙卑又憂傷的人文情懷,裡面尤其包含著他對傷害與原諒之間關係的理解。像〈關於稀土的二三事〉一詩,當是回應核幅射泄漏的議題的。eL不斷列數稀土所沒有的東西,例如「沒有人生」、「不必思考」、「沒有感情的包袱」、「沒有意志」、「沒有娛樂的需要」,卻過得好好的。而這些描述恰恰都是衝著人類對比而言的:你們有感情、有思考、有意志,為甚麼就不明白「稀土本來就過得好好的。)那麼幅射/哪裡來?我們什麼都有,死了就什麼都/沒有。幅射什麼都沒有,慢慢就什麼都有了/它。」最後,eL不忘尖銳地提問:「但其實稀土什麼都不知道(拜託,它怎麼可能/知道?)我們且原諒它。而什麼都知道的我們/能否原諒自己?」我認為這段提問本可隱藏,使詩更具凝練的勁力,但為何eL要過於露骨地如此點明?這正正是他要求人類直面核幅射帶來的禍害,人非稀土,應對自然萬物以及他人的性命,存有更高的關懷與愛惜。
關於傷害與原諒之間的關係,可謂《失去論》中經常處理的命題,較明顯的有〈傷害過我們的人正在養傷嗎?〉、〈抱歉〉、〈國家興衰史兩大冊〉、〈我們是否必須關於日子的如常?〉、〈那些一個人熙熙攘攘的日子〉和〈這裡〉等。「戰事可以許多,流血只有一種。/糧食可以許多,飢餓只有一種。」是的,方式與手段可以有許多,但傷害只有一種,就是無法避免的痛,或堪名之失去。只是,有多少人面對這種痛,會認真的凝視傷口,而非藉「時間會沖淡」等虛謊欺騙自己傷痕已然撫平?「抱歉,若一切顯得理所當然/而我卻無所適從。」eL拒絕時間和歷史把傷害沖淡,他把原諒重新定義:並非遺忘、或遺忘之幻覺,倒應是「以渙散的眼神/打量新鮮的傷口。」最後,血乾結痂之日,便「是時候讓我將內心的枯葉/整理整齊,反覆練習說再見/這一次,讓我從深情對望/徹底痊癒。」無論對自己、對他人,真正的原諒正是一份拒絕逃避、直接面對的問詢與復和,而非由其被沖淡。
我知道的,這確實很難,尤其當我們對一些人或事恨之入骨、或不敢直面。但至少,我想我可以如此祈願:就是向那些我從認識便已失去的人,尤其這半年來或相熟的、或不認識的,並那些終將隨他們一併漸漸消逝而曾經極深的痛與愛,如此垂眉默唸:「多希望,/你離開之後/你還在。」(〈失去論〉)──因為擁有,總是伴隨失去;但我們卻當牢記失去,以及原諒作為報復之可能。「傷害過我們的人哪,他們/正在養傷。」(〈傷害過我們的人正在養傷嗎?〉)
勞緯洛,2001年生於香港,基督徒,現就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2018年出版小說《卷施》;現間有寫詩、評論。 近來讀到源自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的「憤怒出詩人」,銘記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