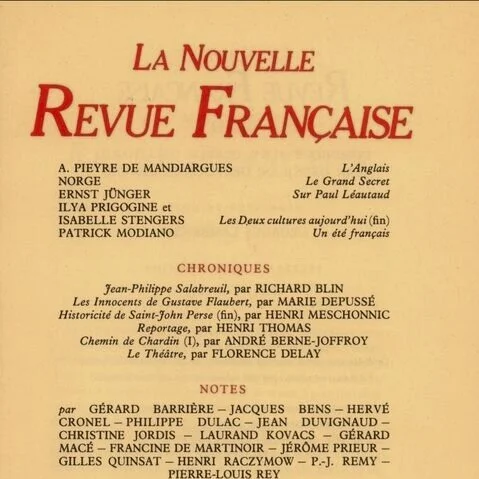所以我會形容為「真正的失語」──不是無法發聲,但我們顯然知道自己「啞咗」。有一天比我們更年輕的詩人,會不會書寫一首〈1997,廖偉棠〉呢(他在那年移居香港)?那時的人回看我們又會是如何?「說吧」是一種持續的期許,期許香港繼續能被言說下去。
2020臺北詩歌節——詩演出《說吧,香港》
相片由臺北詩歌節提供,攝影:林政億
文/韓祺疇
But Hong Kong can’t speak──這是一位身處香港的朋友得知我會到臺北觀看《說吧,香港》後即時的反應,真實而刺痛。在門口取票的時候,詩人廖偉棠恰巧在我身旁,他的詩作是這場表演主要文本;在我的座位正後方,是小說家陳慧;場內還有零星一些廣東話交談的聲浪。我們沒有以香港人的身份相認,這可能是一種香港「啞咗」的象徵,換一個說法就是:失語。不過失語狀態或許只是個體的艱巨,出於外在的低氣壓環境或內在情緒的紊亂,而陷進無法言說的處境,但這場近九成坐滿的表演可以證明,香港尚在發聲並且被傾聽著。
那麼,「如何說」就成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說吧,香港》由鴻鴻策劃,選用了廖偉棠15首書寫香港的詩作,由1810年寫到2020年,文本裏充分可見廖偉棠對香港歷史梳理所花費的功夫,無疑他對這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有充沛的情感。這組詩以清末海盜鄭一嫂、學者魏源、妓女蠻雲,呈現那時香港尚未鮮明(甚至尚未誕生)的形象,再到過客文人蕭紅、張愛玲,而六七暴動、保釣運動、八四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一四雨傘運動、一九二零反送中運動這個重要事件,自然沒有在詩選裏缺席。這樣的選取很完整,包攬歷史與待定的未來,對香港以外的觀眾自然合適不過,但還是該提出這只是廖偉棠看待香港的視角,他強調城市的模糊與虛浮,感傷「就在香港,人們把香港遺忘」 (〈一九八四,盧亭的告別〉)。而廖偉棠描述2019、2020年香港的詩作,帶有更濃重的哀傷,像是提早悼念香港消逝,甚至隱隱有某種呼應前作「香港一早已死」的論述,是一個回不去的故鄉,但我不願同意,我那些還身處香港的同代人想來也不會同意,我們無疑都好鍾意香港,然而生長的年代還是決定了我們各自對這座城市的理解,只能說愛與愛不盡相同。這兩首詩沒有像組詩裏書寫其他年代的作品所展現,充分抽離後再代入其中的視野,這固然是因為我們身處當下而難以擺脫情緒,所以我會形容為「真正的失語」──不是無法發聲,但我們顯然知道自己「啞咗」。有一天比我們更年輕的詩人,會不會書寫一首〈1997,廖偉棠〉呢(他在那年移居香港)?那時的人回看我們又會是如何?「說吧」是一種持續的期許,期許香港繼續能被言說下去。
2020臺北詩歌節——詩演出《說吧,香港》
相片由臺北詩歌節提供,攝影:林政億
整場表演最使我促不及防的,不是結尾部分表演者們慎重地唸出6.9、6.12這連串的數字,而是中段播出梅豔芳、張國榮在演唱會上合唱〈有心人〉前的交談片段──是的,這首歌的作詞人林夕,與廖偉棠、陳慧一樣都已經移居到臺灣。當音樂人黃衍仁唱出「曾忘掉這種遐想/這麼超乎我想像」,接續是賽馬評述的背景聲,演員鄭尹真和禤思敏分別以國語和英文讀出那些歷史文件所言明,對香港生活方式保持不變的承諾。如今回看當然是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嘲笑這段歷史,而實質我們卻是被這些歷史戲弄着。音樂、表演與文本的交流貼合,拓展了詩作的想像空間,產生情感共鳴或延展出反諷的趣味,我得坦誠自己無法認齊全部樂器、曲風和表演手法,所以就只能用一個業餘觀眾的角度去評論其中的配曲和劇場語言,就是:精彩。
今晚的臺北剛下過一場雨,走回旅館寫稿的途中,想起舞台上那幾把用作表演、被剪得破爛的傘,都只是道具,不會是我們心裏的香港。
2020.9.26晚上於臺北
《說吧,香港》
《說吧,香港》
時間:9/26(六)19:30
地點:中山堂中正廳(臺北市延平南路98號)
策畫:鴻鴻
主持:楊佳嫻
文本:廖偉棠
導演兼音樂統籌:黃思農
音樂創作:黃思農、黃衍仁、曾韻方
演員:鄭尹真、禤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