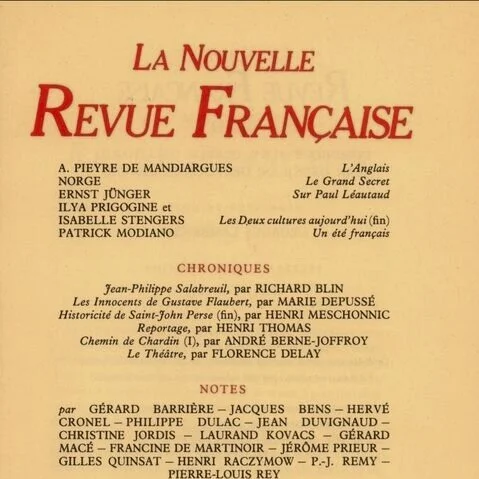當我們談的是文學時,何不先處理美的問題,把其他先放入括號裏;這並非鼓勵逃避責任,只是之後再處理。事實上,世界從來都是複雜,如果不斷受「野蠻」束縛,也許連詩也寫不成,放入括號之後還會有拆開的一天。
文/吳芷寧
生於「亂世」之下,我們就像被置身在「革命」與「抗疫」的時代裡。可是,當「抗爭」變成我們的「日常」後,又可曾思考過自己如何在這種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長期處於「抗爭」的焦慮下,也許靜下來閱讀帶來的經驗反而會預示各種生存出路。試想「亂世」即使可以令我們連出外的自由都被限制,但書本依然在字裏行間透視了現在,也可穿透過去與未來。
雖然大家不能如昔日般聚首一堂,但香港文學評論學仍然跟大家用Zoom「四圍閱讀」。2020年3月14日率先以馬世豪博士主持,由鄧正健博士談談「亂世好讀是殘忍的?」,探討閱讀到底能否與「亂世」扯上關係,成為一股力支撐生命的力量?
亂世書寫:文明與野蠻鬥爭中換來的救贖
活在亂世的旋渦中,要靜下來讀本「好書」並不容易,更何況寫首「好詩」。阿多諾(Theodor.W.Adorno, 1903-1969)曾經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1],鄧正健也抓緊這句話與當下景況的相似點,展開亂世寫詩的討論。他指出解讀時結合上下語境,就會發現阿多諾批判的是,奧斯維辛喚起了人類文化的進程中,文明與野蠻不斷鬥爭的事實,就算文明到有寫詩的能力,結果還是回到野蠻去;因此人們應該上前抗爭到底,而不是在後方不道德地寫詩。這裡不禁讓人生起疑問:難道在亂世之下連寫詩也是不被允許嗎?鄧正健隨即引述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所寫的《死亡賦格》,認為這是對阿多諾的回應,證明如何「野蠻」地寫詩: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
我們中午喝早上喝我們夜裡喝
我們喝呀喝呀
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躺下不擁擠[2]
這段文字刷新了過去文學只會談「美好」的印象,原來「黑牛奶」、「掘墳墓」這些不堪的景象都可以當題材。試問亂世之下哪一處沒有「黑牛奶」呢?用詩的語言把它們寫下來,對創作或閱讀者而言都是直面人生的做法,所以詩為個人而生,也為他人而生。阿多諾見到策蘭的表現後,他意識到「奧斯維辛後你不能寫詩」是錯誤的,原來人可以野蠻地寫詩,而且這種野蠻正正是文明之下的非常態表現[3]。鄧正健解釋,阿多諾本來可以直接否定詩,而且這樣面對的矛盾可能會更少,但他關懷的除了是抗爭之外,更多的是人還可如何生活下去,尤其那些災難倖存者。
轉換一下問題,當亂世中的生活都是野蠻時,我們應否同樣野蠻起來,為對抗惡魔化身成惡魔?鄧正健回應時引用了《浮士德》出賣靈魂換取知識的例子,指出化身成「惡魔」前應當思考背後的原因,為了自己,抑或是為了他人。他按以上更加點出了處於亂世下的兩種理性閱讀: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知識份子責任」;柄谷行人的「公共倫理」。
亂世中的知識分子:站在邊緣彰顯個人道德與良心
知識固然令自己的生活有所改變,但如上文提及,人在亂世之中除了考慮自己外,個人面對世界又是怎樣一回事?鄧正健事嘗試從薩伊德《知識分子論》中「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回應。根據薩伊德所言,知識分子絕不是獨善其身的一群,他們反而是公共與個人的複雜混合體,沒有所謂一己的存在。以寫詩為例,他們的言論一旦發表,就會成為公領域。因此,知識分子一直處於與世界對立的狀態之下。具體來說,知識分子的對立正與薩伊德高舉的個人良心有關。過去談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時,如葛蘭西,都會強調集體知識子發揮力量時對社會的創造性;但薩伊德卻指出知識分子應脫離社會體制,視知識為個人抒發道德與良心的力量,從而揭示社會真相。
這種思考更加引伸至另一問題,知識分子既然是處於社會的一部分,其本身以至文學書寫等各方面,又在怎樣的公共倫理下直面世界?鄧正健借用柄谷行人「括號」的概念,又回歸寫詩是野蠻的問題。
亂世中的公共倫理:為文學加上「括號」只是回應更遙遠的「他者」
當「寫詩是野蠻」只是我們對野蠻社會的回應時,在倫理道德中又能否被接受?柄谷對文學中的「惡」就提出了有趣的觀點,文學中觸及惡早由弗洛依德開始就是眾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這一概念下出發,寫詩是野蠻不過是人類表現原始欲望的天性。鄧正健更加借用柄谷在處理文學時加上「括號」的做法。柄谷認為倫理固然重要,但當我們談的是文學時,何不先處理美的問題,把其他先放入括號裡;這並非鼓勵逃避責任,只是之後再處理。事實上,世界從來都是複雜,如果不斷受「野蠻」束縛,也許連詩也寫不成,放入括號之後還會有拆開的一天。
而且公共倫理處理的不僅是善惡道德,更多的是回應沒有實體的「世界公民」,柄谷用到「他者」的概念,如上文提及,我們既是自己,也無時無刻為他者。不過,我們與他者的對話永遠都是不平等,因為「他」除了是現世的人,也可以是過去、未來的人;而我們的倫理也應該考慮到這些不被納入群體的人之位置。文學書寫也許是回應着遙遠的他者。最後,鄧正健也黯然地引用楊牧先生詩作〈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由楊牧先生離開我們一刻,他成為了「他者」,詩中「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指那個「現實」亦然[4]。而我們在抉擇中,尤其在亂世之下,又能否考慮「他者」留給我們,或自己有甚麼留給往後的「他者」呢?相信這也是當下倫理一個重要的課題。
結語
閱讀穿透了亂世的表象,更能發現自己身處的時代。不過,人的責任是否只有自己,能否在抉擇時考慮他者,包括那些過去與未來的人?文學也許就這種特別的回應方式,不管是野蠻、美麗各式形態,都是人類安身立命之所。
作者簡介:吳芷寧,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生。喜歡中國文學批評及繪畫,偶爾創作漫畫。
[1]語出阿多諾(Theodor.W.Adorno)《棱鏡》.〈文化批評與社會〉。
[2]詳見策蘭(Paul Celan)《死亡賦格》,孟明譯。
[3]詳見阿多諾(Theodor.W.Adorno)《否定辯證法》。
[4]詳見楊牧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如想了解更多楊牧作品,可参考:https://www.literaturehk.com/new-blog-45/202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