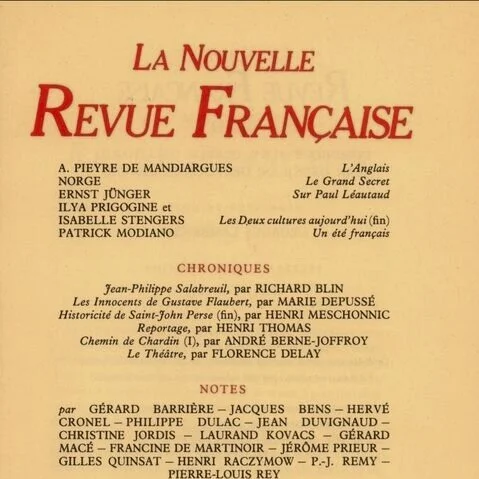這齣電影不信宗教、不信科學,反而肯定人性原始的感覺,我想這不是迷信,而是荷索相信哪怕時代怎樣發展,人性底層的善與惡都會存在。在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中,善與惡或不易見到,當瘟疫來到時,真實的面貌便顯露。
《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
文/黃淑嫻
荷索 (Werner Herzog) 導演的《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在網上的版本雖然不太清晰,但在瘟疫期間,也不能要求太高了。我喜歡《吸血殭屍》這個故事,不是因為任何與殭屍有關的嚇人情節,老實講,現在經驗豐富的觀眾,哪會給殭屍的尖長指甲嚇倒呢。
吸血殭屍,開始的時候,據說是一個真人,然後愛爾蘭作家 Bram Stoker (1847-1912)把故事虛構化,寫成小說 Dracular (1897),一紙風行。在 1922 年,我非常喜歡的德國導演茂瑙 (F. W. Murnau)把小說改編成默片,這應該是很多影迷心中的永恆經典了。電影中的光與影,彷彿是魏瑪電影 (Weimar Cinema)對當時動盪社會的回應。不是每一部小說都好命,《吸血殭屍》算是非常幸福的了,有性格的導演不斷改編,如 Herzog和Coppola都改編過,大家好像誓要把小說愈改愈好。雖然荷索認為這只是一本中庸小說,但這麼多高人改編, 當中必定有它的吸引力,如果我是 Bram Stoker,我一定很高興了,雖然版權之事沒有解決。在眾多的電影改編版本中,我還是最喜歡荷索的改編;至於茂瑙,他有太多更好的電影了。
Bram Stoker (1847-1912)小說作品 Dracular
昨晚在家重看《吸血殭屍》,不記起第一次看是什麼時候了,但一定是在 1997 年之前,SARS 還未來的香港,這好像是上一世的事情了。在微弱的燈光下,我一邊看電影,一邊寫以下的筆記。
1. 旅程
旅程是電影重要的元素:人的旅程,病毒的旅程。放在現在的講法是病毒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吧。我實在太喜歡電影旅程的部份了。男主角 Jonathan Harker 是房屋經紀,他與妻子 Lucy 住在德國北部的 Wismar (但實際拍攝地點是荷蘭的Delft),他的老闆 Mr. Renfield 接到一單大生意,住在Transylvania (羅馬尼亞中部的森林區)的 Count Dracula 希望在 Wismar 買房子,Jonathan 為了給妻子更舒適的生活,答應拿合約到 Translyvania ──一個只在地圖認識的地方。這樣他便開始了「東方」之旅, 從一個「文明」的西歐到「落後」的東歐 。
荷索擅長拍攝野外世界,在他的鏡頭下,東方之旅其實並不恐怖。Jonathan 騎馬來到一個客棧,遇到很多吉普賽人,他們的說話,他不懂,但他們是友善的,希望他不要去古堡送死。Jonathan 離開客棧至古堡的一段旅程,是異常美麗的一段影像 :沒人煙的野外,山中急流、霧中高嶺,海邊窄路。荷索以長鏡頭捕捉光與暗的變化,欣賞陌生地方的自然與神秘。從人物的角度看,好像是深不可測,但其實一切是如此自然。莫非這只是出於人的無知?
電影中的西邊和東邊其實是沒有明確的界線。Count Dracula 是來自東歐森林的不死之鬼,他帶著 10000隻老鼠漂洋過海來到德國,瘟疫便在城市蔓延。Jonathan 因為被吸血,雖然幾經辛苦從古堡逃脫回家,但變得神志不清。最後當 Count Dracula 在清晨第一線光死去後,Jonathan 繼承他的位置,再一次騎馬,遠奔異鄉,好像要回到那個古堡,延續吸血的故事。這是荷索新加的結局,當然我相信他不是為了拍續集,他好像要告訴我們瘟疫並不止是源自一方,可以轉移,是一種共謀下的現象,而且不會停止,在某時某日病毒又會從來。
(《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電影劇照)
2. 古老
我在筆記中寫了古老二字。古老的世界才是這故事的主角,不是 Jonathan 所活當下的社會。Count Dracula 代表舊文化,走進他的城堡,就好像走進古代時空。飾演 Count Dracula 的是著名演員 Klaus Kinski,他的舉手投足都充滿怪異卻非常優雅,很有趣的結合。這個人物可以很多發展,怪不得在往後 Coppola 的改編中,吸血殭屍變得更立體。古老的感覺也來自荷索向茂瑙的致敬,Isabella Adjani 飾演的女主角和 Klaus Kinski 飾演德古拉,二人的化妝和表演方法都極像默片演員,大家好像同時在看有聲電影和無聲電影的感覺。
然而,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荷索在1970 年代末拍攝此片,當時正是上太空、科學探索的年代,與古老幾乎是相反路向,但電影借 Lucy告訴觀眾不能盲目相信科學。病毒就好像是最古老的東西,牠可以從最遠古的森林走出來,讓靜止的時間活起來。如果 Count Dracula 本身就是古老病毒的形象化,那麼,不滅的慾望會把埋藏的病毒從森林的深處翻出來,Count Dracula 不是看了美麗和純潔 Lucy 而決定來 Wismar 的嗎?這齣電影不信宗教、不信科學,反而肯定人性原始的感覺,我想這不是迷信,而是荷索相信哪怕時代怎樣發展,人性底層的善與惡都會存在。在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中,善與惡或不易見到,當瘟疫來到時,真實的面貌便顯露。政府官員四散奔走、染病的大眾只能無助地狂歡,而 Lucy 良善果敢的性格在這時候展現出來。瘟疫的來臨是要撕破日常生活的面具。
(《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電影劇照)
3. 感應
我寫下的第三個詞是感應。荷索曾在一個訪問中說道,這故事是關於溝通,這主題在原著小說中已經出現。小說以日記及書信體方式敘事,由不同人物敘述自己的故事,這些人物寫下的文字都是希望與人溝通,例如 Jonathan 被困在古堡中,寫下所見所聞及內心恐懼,希望日後 Lucy 能看到。然而,我覺得電影中最有力的溝通方法不是文字,而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感應」。
電影開始的時候出現了蝙蝠,然後 Lucy 在夢中驚醒。在瘟疫還未正式來到之前,她已經感應到黑暗的一方,預知某些事情會發生;她還有夢遊等習慣。電影在拍攝 Count Dracula 和 Lucy 時都有不少平衡對照,例如兩人同在城市的廣場奔走,前者在散發病毒,後者在拯救社會。Lucy 在電影的下半部是主角,代替是 Jonathan 的位置,因為她有感應,她用自己的方法希望可以解決瘟疫。當中有一場戲她一個人走到廣場,被成千上萬的老鼠群中 (不是 CG 呀)包圍,看到社會眾生相,高官不理民情,民眾無知的實況,她最後決定犧牲自己,這一場讓人難忘。在 70 年代女性主義抬頭的歲月,這劇本有時代特色。
我在筆記中寫下最後的一句。最古老的病毒,也會演變成最尖端的殺人武器。當人類的慾望擴張,病毒會從最遠古的森林爬出來。(16-2-2020)
在海邊凝望死亡的 Lucy (《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電影劇照)
黃淑嫻,作家、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現任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範疇包括文學與電影、香港文學與文化。 出版散文集《理性的游藝:從卡夫卡談起》(2015),及與攝影師合作的散文攝影集《亂世破讀》(2017)。 短篇小說集《中環人》(2013) 獲第25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文學與電影論文集有《女性書寫:電影、文學與生活》(2014) 及《香港影像書寫:作家、文學與電影》(2013)。主編「一九五O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六冊 (2013)、《香港文學與電影》(2012)、《香港.1960 年代》(2020) 等。曾任「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片系列之《1918:劉以鬯》(2015) 及《東西:也斯》(2015) 的文學顧問及聯合監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