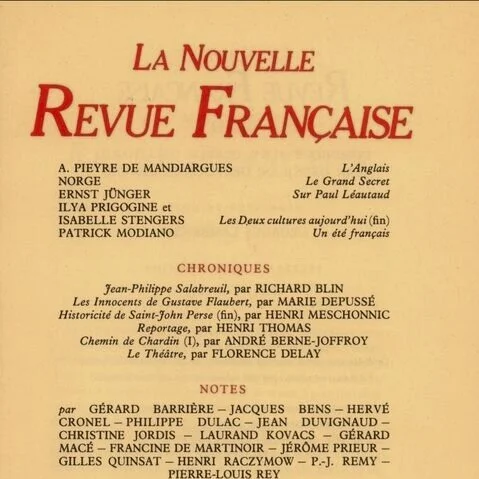活動尾段,有十數分鐘浸沉在〈山伯臨終〉前的氛圍,無論是嘆息或呢喃,既是懊悔也是懺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而粵劇唱說之技巧展現,引導觀眾專注言語中所盛載的情節及細膩情感。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演員、粵劇編劇文華小姐演繹改編劇目《梁山伯與祝英台 》的〈山伯臨終〉選段。
文/蔡寶賢
再寫山伯臨終超越性別概念
粵劇文本具不同賞析角度,亦有文學可再造與延伸的特質,由對傳統劇目改編再寫,加入新穎的演出元素,可持續為粵劇注入活力。「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演員、粵劇編劇文華小姐最近改編著名劇目《梁山伯與祝英台 》[1]。梁祝故事家傳戶曉,早已被後人多次改編演繹。文華重新審視原劇本,從中找出可以延展的時代意義,加強了梁山伯為門弟之見而心碎的背景。文華撰寫的〈山伯臨終〉一折,當中山伯知悉英台女兒之身的一段內心獨白:
可知我心念卿卿思賢弟,妝台遠望,聊慰心靈。
可知我長夜盼卿卿,坐看天明,喚卿卿不應。
山伯直面自我內心對「賢弟」思念之情,知悉祝英台是女兒身,倒反失去「賢弟」,故而思念。文華憶述此部份是「超越性別的概念去創作」,人倫之愛的培養與展現並不拘泥於性別定型 ,也為原著中山伯的情感狀態,多添一筆,人物性格更見鮮明立體。
粵劇電影《新梁山伯祝英台》(1951)任劍輝飾演祝英台。
說唱盛載延展情感和時間
香港粵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藉唐滌生回歸文學,文華從新改編的劇本選段中帶領觀眾細味作品中的的語言藝術,領略粵劇作為文學的價值。在由沒有衣飾、化粧和舞台佈置下,聽著文華小姐演唱〈山伯臨終〉選段,專注聆聽其歌唱演繹。
活動尾段,有十數分鐘浸沉在〈山伯臨終〉前的氛圍,無論是嘆息或呢喃,既是懊悔也是懺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而粵劇唱說之技巧展現,引導觀眾專注言語中所盛載的情節及細膩情感。我仍要手拿劇本,跟字慢讀才能明瞭山伯鬱結所為何事。但這次我能專注其中,發現粵劇能帶人抽離日常急促又重覆的生活模式中,以藝術表演方式帶觀眾代入、感受和理解角色的情感態狀,填補繁忙城市生活中經常忽略的人性人情。
《香港粵劇編劇家作品之文學性與劇場性:唱做唸打演故事》講者與香港八和會館總經理岑金倩女士合照。
聽曲看戲是閒情,閒情之意,即是有機會或意願花時間感受角色情感的流動。喜怒哀樂,七情六慾,人之常情;現代城市生活,為了保維持高生產力,要維穩,我們要保持理性克制,常情又變得疏遠陌生。若然粵劇當前困局是要尋找更新與持續傳承的推動力,著力提煉出劇本的文學及語言價值固然其一,而它的情感教育的能力也可能是另一可行出路。
這是我第一次聽現場演唱的粵曲,也是我第一次對粵劇文本如此咬文嚼字。所以沒有聽過陳笑風〈山伯臨終〉的經典版的包袱。整晚演講和演唱走非傳統的粵劇講解的路線,先引導參與者回顧粵劇發展,再學習劇本賞析,並在現場演出中體驗說唱的藝術展現。一直由淺入深,帶領著大家認識粵劇,會中無論是戲迷或如我一般的初哥,在場都能發現當中引人入勝之處。它的可能性,真的仍然多得不勝枚舉。
編者按:本文是《香港粵劇編劇家作品之文學性與劇場性:唱做唸打演故事》的評訪下篇。
作者簡介: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海浪裏的鹽——香港九十後世代訪談故事》作者;現為藝文記者、編輯及藝術行政自由工作者。
[1] 文華改編《梁山伯與祝英台》,關注故事產生在沒有科舉制度,卻以門閥將人分為世族(高門)及庶族(寒門)的魏晉時代。那時庶族子弟只能透過名士或望族的推舉,出任卑微的官職。編劇透過重編粵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探討一道高門如何為梁山伯帶來希望,又如何無情地摧毀了他的人生。與其他梁祝粵劇劇本在這主題上稍有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