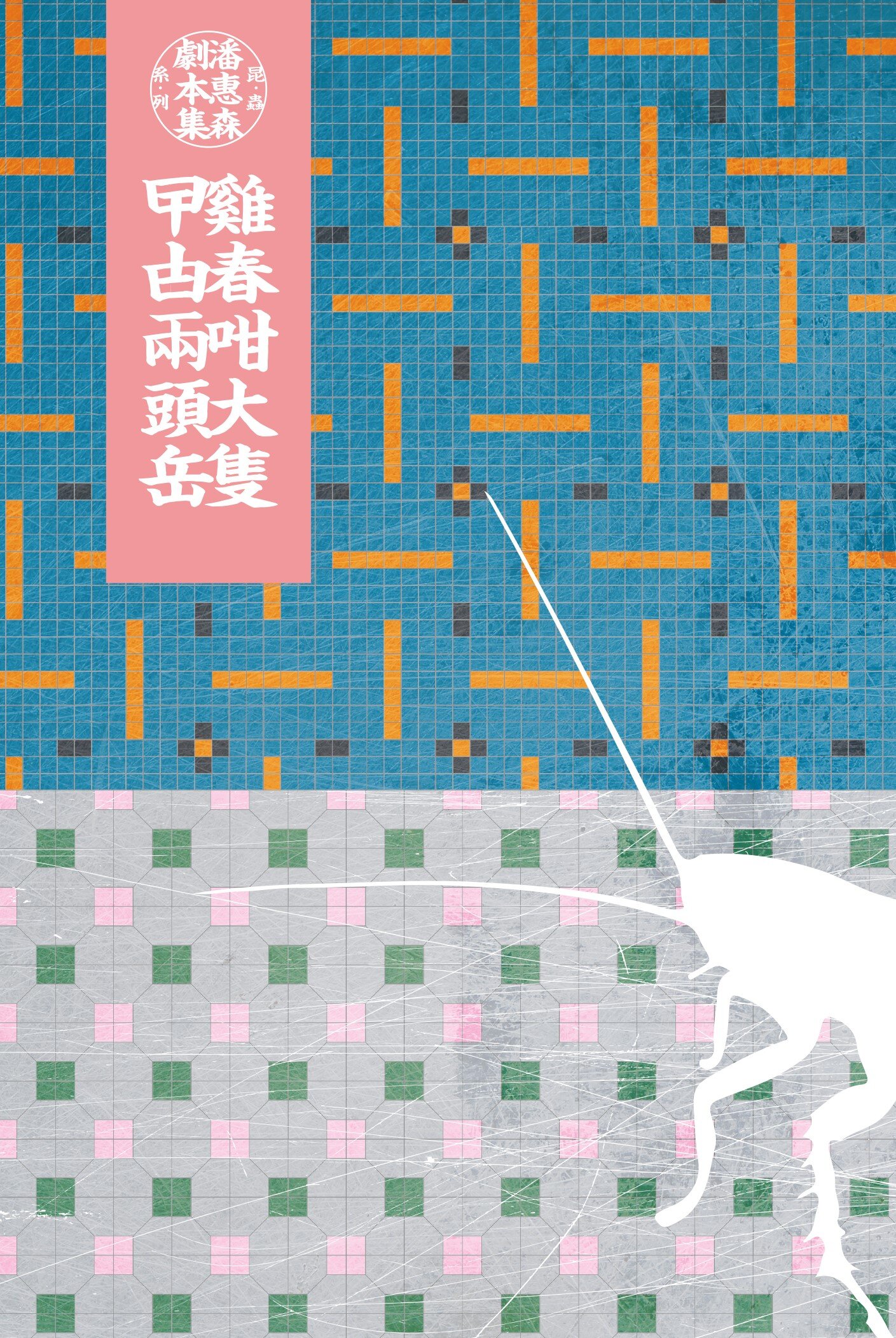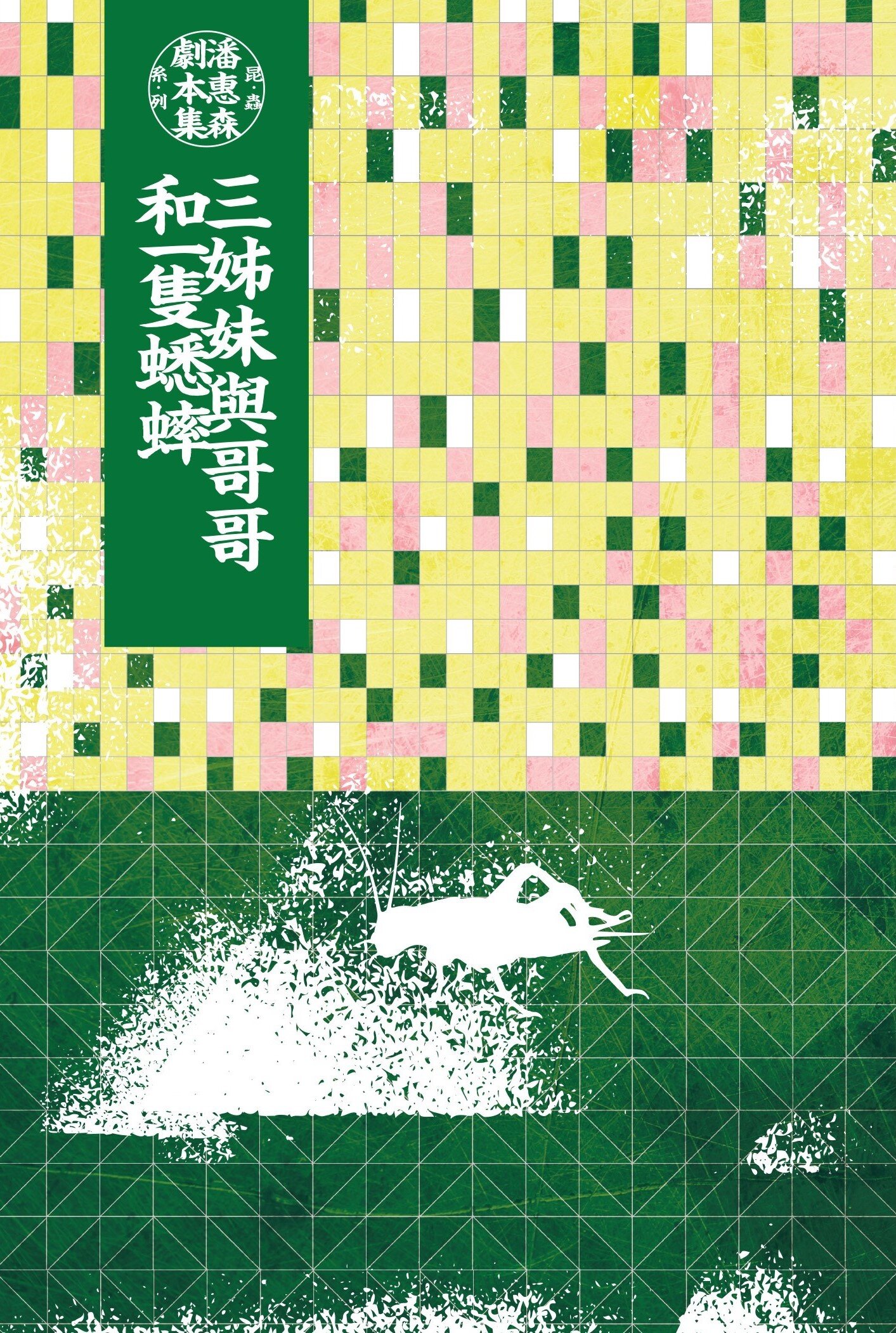放大的絕非生物學意義的,不是在描繪身體結構特徵,而是敘述行為模式,一群生物在特定環境中會如何生活,互動溝通?在困境中如何自處?昆蟲作為喻體,比喻著社會低層被漠視的一群,如昆蟲勤奮求存,為努力工作致犧牲生活,卻被大眾視為低賤而屈居在社區邊緣。
文/江祈穎
拿到放大鏡,除了觀察自己的皮膚組織,就是用來放大昆蟲,平日隨手殺之而後快的附生者,仔細端視其觸角與肢體,是何其獵奇怪異。潘惠森這套劇本,就用放大鏡去直看巿井生活,當日常生活與語言都放大扭曲,尋常百姓一一都變得畸形。
放大的絕非生物學意義的,不是在描繪身體結構特徵,而是敘述行為模式,一群生物在特定環境中會如何生活,互動溝通?在困境中如何自處?昆蟲作為喻體,比喻著社會低層被漠視的一群,如昆蟲勤奮求存,為努力工作致犧牲生活,卻被大眾視為低賤而屈居在社區邊緣。這似乎是社會寫實主義戲劇所關心的角度,但卻非易卜生式的殘酷掙扎,亦非蕭伯納式的幽默超越,潘惠森劇本中,情節始終是缺乏推動,對白欠缺碰撞,而角色亦無解決問題的意志,只呈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狀態。這似乎構成魔幻荒誕的況味,但對比貝克特的虛無形態,角色卻又較富生命力,帶有生活的寫實質感。沒錯,潘惠森就是這樣難以界定,自立方寸。
只有發音的語言
要進入潘惠森的戲劇世界,語言是必不可缺的門徑。對白是角色交流與衝突的媒介,但在大部份劇本中,角色雖然依然你一言我一語,卻總是在各說各話。角色們雖然是互相說話,但總沒有理會對方的回應內容,而不斷提出自己的要求、意見及想法,兩人的言語表面上有題材上的關係,事實上卻互不相干,有時一方停口沉默,另一方繼續自說自話,卻非獨白或長句,而會保留句與句中間的空白,卻又非期待回應,而繼續說話,到最後其實只是用以抒發自己的感受,希望被人聆聽,卻慣性地不聆聽別人,形成多個角色不斷對話,而情節卻毫無寸進,角色們會因最無謂的瑣事而不斷擾攘,或因說話的字眼問題而爭吵不斷,亦可能因整體氣氛而受感染,但個人內心感情卻從沒交流。如哈洛.品特要在對白中滲透生活的危機感,潘惠森的對白則流露生活的茫然,當中絕不荒誕,反而很寫實地呈現出小人物的生活:在工作與繁忙生活中閒聊抱怨,生活充斥對話卻沒有真實交流,故對白其實是十分富生活質感,潘惠森往往在劇中把這種生活絮語拖長至荒誕地步,直到夠長令小人物們說出自己的感受,互訴心聲卻沒有理解與釋懷,一如蟲蟻無人問津。
《潘惠森昆蟲劇本集》
畸形的生活,扭曲的情節
這些小人物活在香港何方?潘惠森尤如進行社會實驗一樣,放置他們在不同場景,從尋常茶檔茶樓的茶客、唐樓一家人,以至平價酒店中的特務等,場點或實或虛,劇情或日常或不尋常,角色或無聊地工作閒著,或有任務在身緊張至極,但無論場景或劇情如何,情節總是鬆散至似有還無:在街巷間小學雞式胡亂打鬧;一家四口為一蟋蟀大吵大鬧;在90分鐘的任務時間裡不斷為早餐而掙扎,結局總是不了了之,由始至終不見任何轉變,只看到不斷重複的生活枯燥,但與抽離時空卻抱有微小希望的《等待果陀》不同,潘惠森的戲劇必然落實於香港一角,在回歸後的五年時空中,這城巿一面殘留殖民色彩的繁華與虛浮,一面卻帶著主權移交的迷途與焦慮,巿民在無法主宰的歷史漂流中失去身份,只能繼續過喧囂與乏力的港式生活,故情節的拖沓與無謂的執著,正對應這種無力感與經驗匱乏,這在《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一劇中達到最大的比喻:一班低層人物秘密相約於天台,搭棚成天橋往銀行:幾乎是港式景觀的大拼湊,卻非打劫,而是尋找一隻蜘蛛,如同曱甴、螞蟻和蟋蜶,這些昆蟲作為意象,可能代表生活尊嚴或自由,但以這些本身極下賤的生物,作超越現實的期盼對象,港人們連昆蟲變形也不能,只能被生活迫至畸形,本身才是最荒謬唏噓。
在語言情節中追尋文學風格,在場景與意象中追尋港式意義,這是潘惠森的戲劇所難以模仿及歸類之處,文本應作為文學的香港戲劇,或是作為戲劇的香港文學?劇本在可演性與文學性之間的摸索,在香港地文化、後殖民時代與香港遺民之間,刻劃出港式浮世繪,精如昆蟲標本集,細如上河圖,卻活如昔日錄影帶,帶著魔幻與寫實地,在香港戲劇史或文學史中留下幾頁,亦總在某時某地重演時,讓我們緬懷一番。
作者簡介,江祈穎,主修文藝學、當代文學及哲學。《聲韻詩刊》活動策劃,《號外》藝評員,網台節目主持,業餘戲劇演員及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