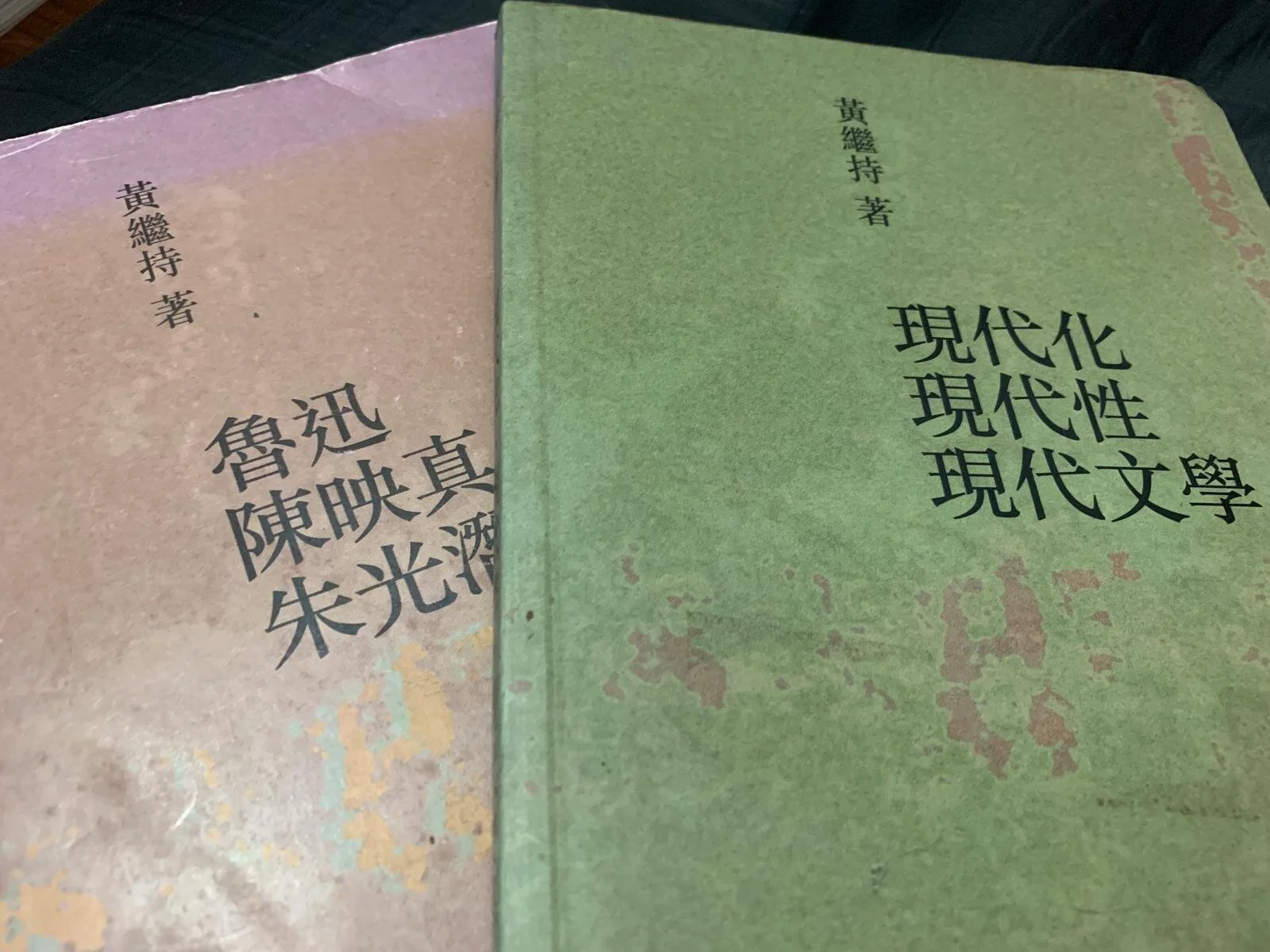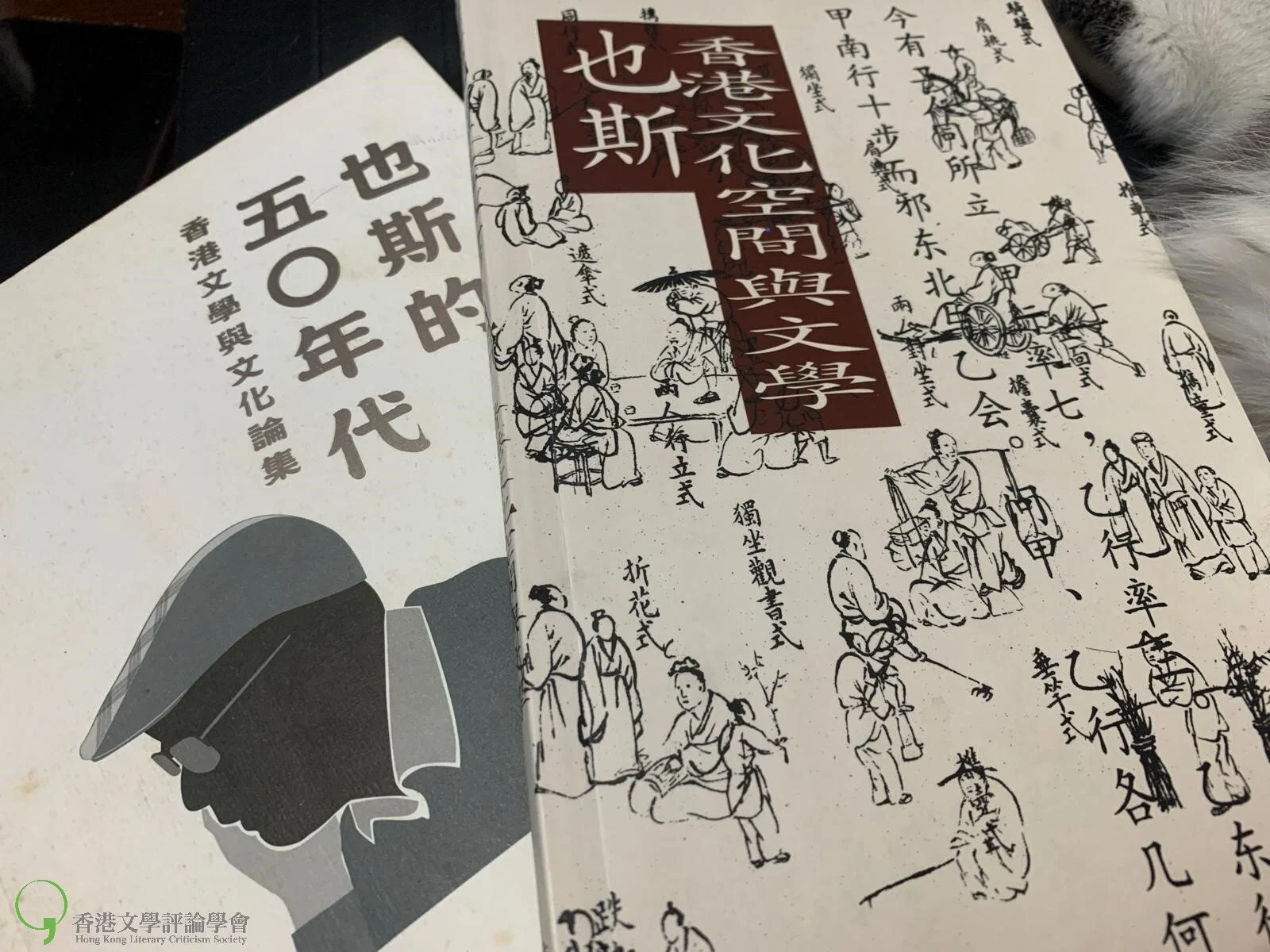有關香港文學的部分,由於香港這一地方海納百川,既中西混雜,又有南來文人避亂等歷史因素,人口組成複雜,在學術上就要細心思考何為「香港文學」。他認為候選條件有﹕香港人寫?在香港寫?書寫香港?最終,他認為「在香港寫」是一個必要條件,確切地說是文章發表於香港的,都可以納入香港文學的範疇。他舉出金庸為例,金庸是最著名的香港文學家。金庸既非土生港人,其故事亦非書寫香港,之所以被公認為香港文學家,源於其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報紙連載。此外,他銳意連結中國現當代文學同香港文學的脈絡,顯出香港文學的獨特,而非像一般大陸學者將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子項置於中國當代文學之下。
文/胡家晉
許子東教授,香港文學重要的研究者。其對於五四文學、當代文學與香港文學,都有重要的研究結果,尤其重點研究郁達夫、張愛玲及黃碧雲,近年開始涉獵晚清文學。
這是一篇關於子東老師治學心得、教學風格和學術觀點的文章。雖然是如斯正經的開場,實為我自身的回憶錄無異。因為我對於子東老師的印象與交流,都源於大學課堂。
他的授課風格輕鬆、幽默。我上他的課時,他已是《鏘鏘三人行》多年的節目主持,因此課上也多有那種吸引聽眾的演說風格,比如他很喜歡講述與當代中國、香港作家的交誼。陶傑、董橋、葉輝、劉以鬯、西西、黃碧雲、黃安憶、余華,都是我回憶他課堂時,會隨之而想起的名字。
嶺大很多同學都喜歡上他的課,原因與這種喜談八卦的風格多少有關。就如大眾熱捧明星偶像,文學系學生的偶像就是各位文壇大師。畢竟故事動聽就足以吸引人,何況還是自己偶像的?在我來看,子東老師只是把兩者的關係作了結構主義式的抽空與理解,把學生——作家/文本——教學三者的關係理解得很透徹。他談及過要打破香港文化沙漠的困境,就要先推廣後提升,估計與他是一位成功的傳媒人有密切的關係。他相信增大受眾的層面與興趣,才能把他們的能力、整體的風氣提升,俗語就是「做大個餅先」,而子東老師對做那個「阿茂」甘之如飴。由此可見,他對香港文學的環境是著眼大局的,學生是不是關心他的研究課題,成為他的忠實粉絲,不是重點。令學生對文學產生興趣才是最有價值,也是他認為最大的教學貢獻。
許子東老師。
此主張連帶影響他的另一教學風格﹕平易淺白。他的教學筆記精簡,對,我們的年代,教授的教材仍是數頁A4,每版幾Point。靠老師的才學支撐課時,也靠學生一紙一筆手腦高速並行。大概新一代的學生會覺得天方夜譚。想到大學建築屹立依然,但內在風格變幻,不禁興嘆。子東老師課堂論點清晰精簡,提綱挈領,外加言談幽默多趣聞,使同學容易領略其要點,便於吸收。
他的才華很早就被肯定。他不多在課堂上講述他求學時的經歷,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在「現代文學批評」課上。他講到文學的起源與本質時,才提及他師從錢谷融的經歷。他憶起第一次發學報的經過,那篇文章原是錢先生佈置的課後習作。子東老師對郁達夫的文本精細閱讀,然後把不同於時人的心得寫下,寫了8000多字,戰戰兢兢交給錢先生。最終,習作得錢先生賞識,略為修改便推薦發表華師大的學報了。他連稱幾句「太順利了吧」尤其令我印象深刻。這段經歷聯繫到筆記上錢先生主張的「文學即人學」,指的是文學就是觀察人類、細味人心、體會人性的一套工具,更進一步就是孔孟所謂透過習文而提昇人品。這句話簡單直白,但博大精深,不是輕易可以領略箇中三昧。從子東老師的回憶與教學,可見他十分認同其師的文學主張。
子東老師曾將他任教的現代文學課堂資料整理,在2018年出版《許子東現代文學課》。
這無疑影響著子東老師的治學態度,他十分強調文本細讀這一個最基本而最重要的技巧。一如他的名作《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敏銳地發現張愛玲與錢鍾書都愛逆向運用意象,但二者同中有異,分別就在於錢氏多用抽象概念喻具體事物,再附帶一段解釋性文字明確說明兩者連接的原理;張氏則反之,多以具體事物喻抽象概念,而且選用之喻體均屬都市及人工物品,現代感強。僅節〈茉莉香片〉的一例說明﹕「她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悒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雲朵裡的一隻白鳥。」屏風是精緻的人工物品,觸手可及且形體明確,屬具體事物,但繡在其上的鳥所失去的「自由」則屬抽象概念。最妙的是,「輕輕的」紗線卻能把象徵自由的鳥「死死地」緊釘屏風。經他點撥,才明白到張愛玲文字之所以能直擊心緒的原因。
強調文本細讀的研究者,自然也容易認同「知人論世」的學術理論。因為研究者在文本線索中找出大量作者埋藏的心思、所造的佈局,自然想盡辦法通盤了解,也就不能忽略作者的生平經歷、身處的社會環境。「別的作家揭破美麗是為了直面慘澹的人生,張愛玲卻在領悟蒼涼之後仍抓住美麗。」大概不是很多人認同子東老師這種對張愛玲文學的歸納。因為這種解釋很「童真」,然而這個講法是準確的。用筆者不算專業的理解是,張愛玲在揭示出人世種種的痛苦與無奈後,她覺悟到日子仍要過下去。在這個爛透的社會下,我們仍要努力而謙卑地過著我們的人生。這就是那層「蒼涼」籠罩全文的原因。用一句張愛玲自己的說話,就是「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想來這種感悟,也是因為張愛玲自幼便受到西學母親的震撼教育所致吧。
2011年出版的《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收錄多篇張愛玲研究的論文。
最後,他也著重運用結構主義研究文學。其力作《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就是文本細讀加上結構主義的研究產物。他對於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甚至哲學理論都不太喜歡,認為這些新式的理論容易使研究者忽略了文本,成為無根之談。他特別重視作者、讀者、文本與社會四者的關係,認為藝術性同社會性成正比。他在講授五四文學時,提到當時兩大藝術主張﹕創造社主張的「為藝術而藝術」,與文學研究會主張的「為人生而藝術」。他談及自己的理解也由年青時喜歡前者,到年長後變成後者,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這一主張,甚至認為藝術性高的文本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
有關香港文學的部分,由於香港這一地方海納百川,既中西混雜,又有南來文人避亂等歷史因素,人口組成複雜,在學術上就要細心思考何為「香港文學」。他認為候選條件有﹕香港人寫?在香港寫?書寫香港?最終,他認為「在香港寫」是一個必要條件,確切地說是文章發表於香港的,都可以納入香港文學的範疇。他舉出金庸為例,金庸是最著名的香港文學家。金庸既非土生港人,其故事亦非書寫香港,之所以被公認為香港文學家,源於其武俠小說在香港的報紙連載。此外,他銳意連結中國現當代文學同香港文學的脈絡,顯出香港文學的獨特,而非像一般大陸學者將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子項置於中國當代文學之下。
因此,他能慧眼識出黃碧雲的獨特,多年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都錄入其作。他尤其欣賞〈失城〉,特意創立「失城文學」這一術語。眾所周知,寫出名作已不易,作品能成為術語就更難能可貴了。子東老師認為黃碧雲以《失城》為首的一系列「失城文學」,類近「傷痕文學」,屬於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港人獨有的痛苦。這種殖民地政權交接的不安與前途未卜的恐懼,黃碧雲透過筆下人物的病態、性愛、暴力、殘殺等「荒謬」內容,有意與「末世」的意象相結合以刻劃主權移交帶給港人的傷痛。
許子東老師編選的《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他在〈序言〉表示非常欣賞黃碧雲的小說,並創立「失城文學」的術語。
最後,子東老師十分關注香港文學中的中港關係,也是其研究的特色。可能與他自身的獨特身份也有關,他也屬於一個南來香港的文人,只是其文盡在學術而非創作。在香港,他被視為中國人;在內地,他又被視為香港人。這使他對香港文學,甚至香港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又不會有偏見地看香港。
作者簡介﹕胡家晉,中國社科院博士生,大專講師。經營Instagram文學帳號(@ineichashitsu),熱愛文學、藝術及烹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