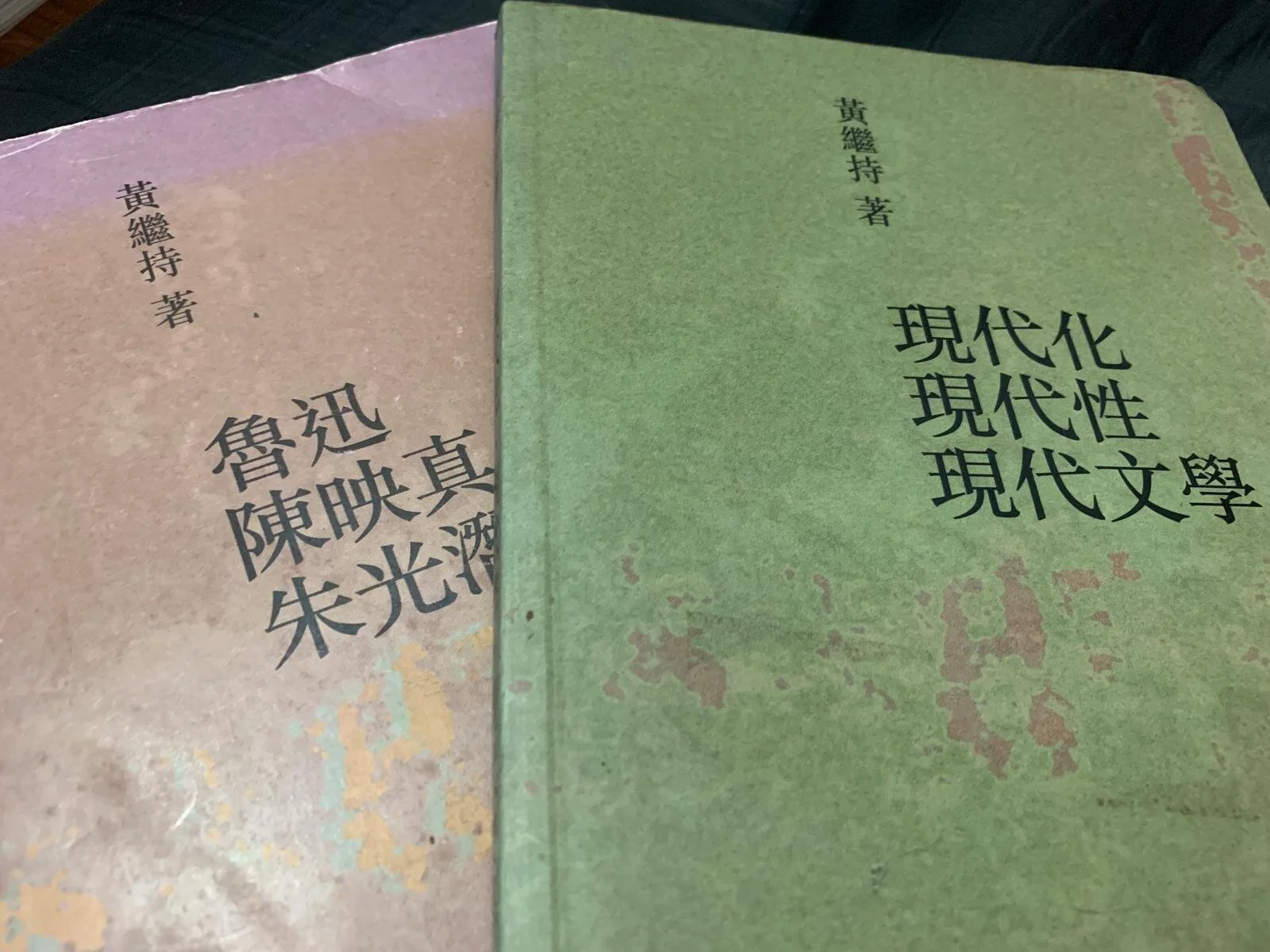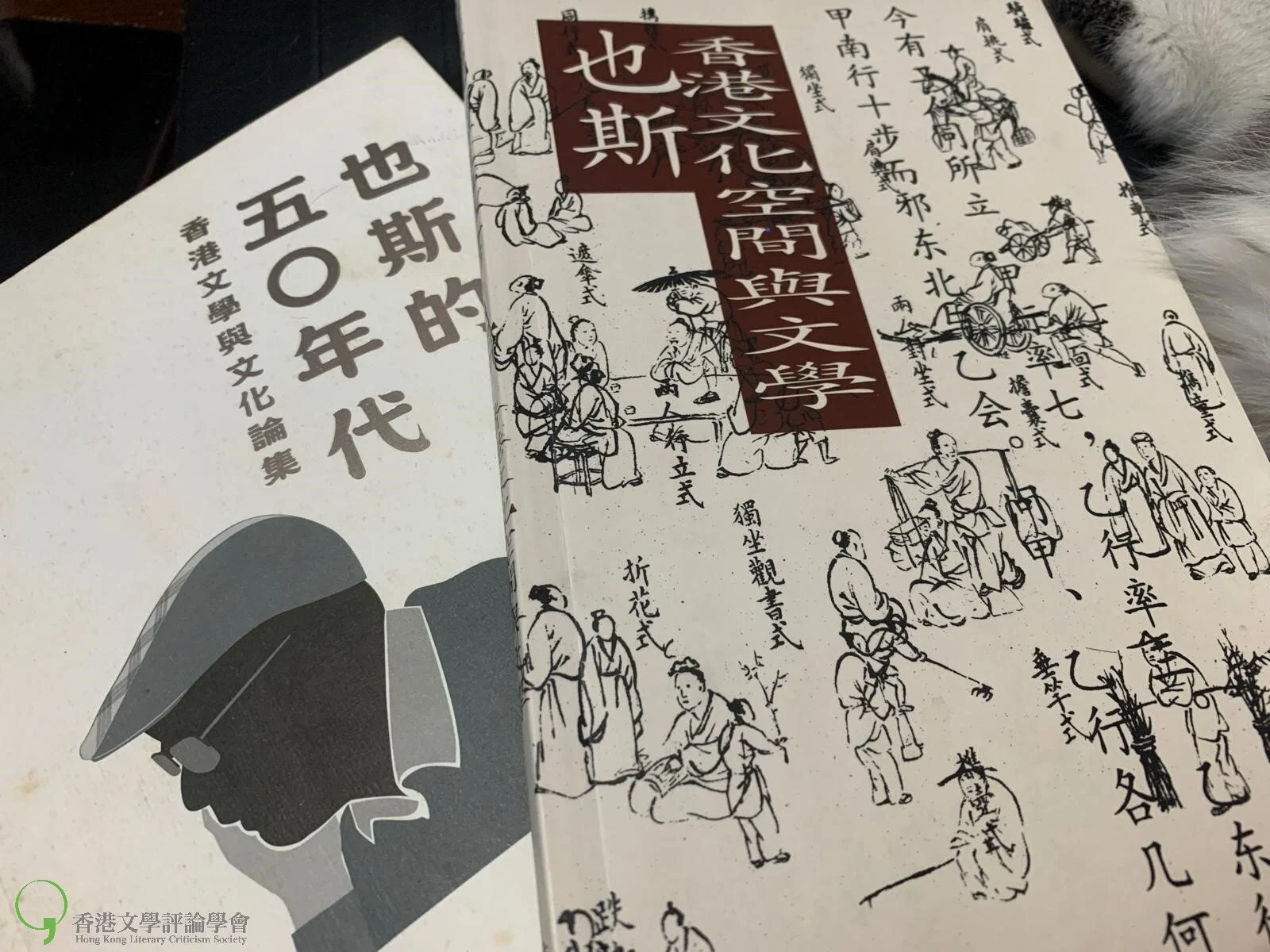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
文/趙傑鋒
李歐梵是我在中文大學念博士時的論文導師。身邊很多同學習慣叫自己的論文導師為「老闆」,我卻只叫他「老師」。他有些弟子會直接以英文名字稱呼他,我卻一直不敢這樣叫他,一來是出於尊敬,二來我認為叫「老師」更為合適。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止是學問,還有各種待人處事和對工作——尤其是學術——的態度。每次見到老師,總是有一種請教或是傾訴的念頭,儘管畢業了,我們還保持非常緊密的聯繫,每次見面聊天他總給人無限動力。如果說他是「老師」,也許他在我心目中更像是「父親」。李歐梵總是有一種這樣的魅力。
李歐梵這名字早已人所共知,他的求學和教書經歷在牛津大學出版的《我的哈佛歲月》中早已詳述,不容我多作闡釋。他是美國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祖師,這亦舉世皆知。本文是我作為他五年的學生、助教和研究助理的一點個人經驗,文章以「雜憶」為題,只求把一些有關老師的記憶在褪色前記下來,我的能力也僅此而已。我大學畢業不久剛進中大工作時,便早已在不同的圖書館講座、書展和課堂上聽過他的課,也曾戰戰兢兢地索過合照。真正接觸到他的學術和方法,是在修讀博士初期他的一堂研討課上。
研究的起步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
李歐梵的講座我早已旁聽過很多次,他亦從不拒絕任何人旁聽。第一次正式「上課」,是在我剛入學中大博士的一年。那年是2015年,剛好是二戰結束七十年,老師以「戰爭與記憶」為題,開了一門研究生的研討班(seminar)。我以修課學生之身分,名正言順選了這一課。剛開學不久,便發覺他的課與我經驗中的一般大學課堂與別不同。老師與他的一位德裔博士生合作,以德國的二戰歷史為主題討論戰爭與文化記憶,那時我對德國的興趣還不大,知道也不多,只記得幾本指定讀物,包括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的《一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和彼得貝克(Peter Burke)的《知識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都是較為平易近人的歷史學術著作,讀起來津津有味。
過了首四堂,老師便要求我們做「功課」。課堂作業除了期末論文外,還有一個簡報(presentation),長約半小時,題目自訂,但要與課堂主題有關。沒有任何指定方向,要自己找資料做研究,看甚麼書也由自己決定。這可頭痛了,一來我當時對德國歷史認識不多,二來我對有關「記憶」的理論掌握不深,不可能在短時間作一個有關德國的深入研究。那天正徬徨,在大學書店漫無目的遊蕩,無意中找到了一系列有關香港二戰時期的「老兵」口述歷史,有關香港的抗戰歷史一直都是一塊缺失的拼圖,當年「口述歷史」的流行也正好與課堂的「戰爭記憶」主題不謀而合,便決定用香港抗戰記憶作為我簡報的題目。那數個星期間一口氣在書店、圖書館找來一大堆有關香港二戰老兵的資料狼吞虎嚥,到頭來卻找不到論點,只好把找到的資料和書目在簡報中略加說明。資料有一大堆,卻毫無邏輯可言。開始簡報時,冷汗直流,緊張得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以一般的大學課堂的標準,我肯定會拿個「零雞蛋」。
李歐梵教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漢學界的重量級學者。他曾在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與讀者分享如何在全球化下的保持人文素養。
結果卻出人意表,老師對我的簡報讚賞有加。記憶中他站起來,漫漫走過來跟我聊了幾句,魂不附體的我早已忘記他的評語,只記得其中的一句:他希望這題目是由他的學生做出來。但是,這個一點邏輯都沒有的簡報有甚麼值得研究?其他同學的簡報條理分明,理論運用遠超於我,老師卻似乎興趣不大。只記得當時聽了他的話我一時呆立,不懂得回應。往後成為老師的學生後,才發覺這是他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在起步階段很多時都是一大堆不連貫的資料,如何從資料中提煉出一個好研究才是一門功夫,否則如果只看理論和二手研究,所有「研究」都會千篇一律。老師常對我說:要是掘到一塊石頭,便要想辦法把它雕成珠寶。這也是他對歷史資料的執著,也奠定了我研究戰時電影的興趣。
老師的教學魅力
除了研究生的課,老師也有一門名為「中國文學經典導讀」的課,每年開一次,是一門本科生的課。課上老師要求學生看原始史料或文章,如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和胡適的《四十自述》(但我很懷疑有多少同學有認真看過)。這樣做是希望學生不會先入為主受其他人的觀點影響,他亦要求學生在功課中多提出個人觀點,不要盲目跟隨或套用理論。看書要讀原文,不要看翻釋。這也是他為甚麼多次鼓勵我學外語,也是我在他身上學到最重要的態度。
幾年來,老師本科生課堂都定在下午。他每次都在上課前十分鐘到達課室,揹着一個破舊的書包,裏面總放着幾本與課堂有關的書,上課前拿出來,放在旁邊的小桌子上,卻很少用。上課時他坐在課室中央,隨身有一張只有他看得明的手寫講義。我有幫忙做過「PowerPoint」,但只供參考,老師在課上總是隨心所欲,行雲流水,有時甚至不按幻燈片次序演講,一說便是兩小時,聲如洪鐘。李歐梵每年的課——儘管課堂名稱一樣,內容也不盡相同。他曾對我說,這是他對「教學」的要求,也是對學生負的責任。每年的第一課,他都緊張得睡眠不足,大清早起牀改講義,直至上課前十分鐘才給我「最新版本」。儘管老師對格式要求不高,但偶爾我還是要修改格式、圖片、顏色和字型(前一晚我本已校對好),這是件趣事。
李歐梵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挫而彌堅」。
談到論文,老師總不用講稿,侃侃而談最少兩小時,起初每次見面,我都在他辦公室坐上幾小時。往後為省車程和時間,便乾脆到他家裏去談。每次到他家裏,他總會預先泡好茶,坐下來,先聊一些生活瑣事,再談論文。給他一篇文章初稿,他都會認真看完,打回頭時寫滿評語。有次趕交稿限期,匆匆趕就文章給他過目,看完後他生氣得很(他說沒有),當然我對他的評語沒有任何反駁,反而心感歉疚,我明白這是他一直對學術寫作抱有極高要求之故。此後我朝乾夕惕,提醒自己不再倉猝寫作,寫的東西要有「commitment」——我「入門」時李歐梵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有時聊得晚了,師母會親自下廚,留我吃晚飯。有時晚飯後,老師會留我與他一起看影碟或音樂會。這些都是極美好的回憶。
從整個時代進問題的脈胳
有關學術,基本上任何題目老師都能從容回應,從不把任何話說盡,亦不會給一個「標準答案」,「李歐梵」的方式是以提問引導思考。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從不被一家之言所束縛。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老師不從問題直接入手,而是把問題的連繫的「脈絡」(context)釐清。從一整個時代進入,逐步收窄和歸納,而非以流行理論作演繹。老師非常重視理論運用,常警惕我:理論有脈絡,也有歷史,使用時要小心。或許有人會片面地把這理解成一種反「(西方)理論」論調,事實上並非如此。有次我不求甚解,把一個位法國學者的理論寫在我的初稿中,老師讀後馬上指正,並指出我在有關理論內容和脈絡的誤讀。
如果學問是一套武功(人文學科中常有這個比喻),那麼老師的套路便有點像金庸筆下的「獨孤九劍」,像是一套千變萬化的方法,而非一套固定的模式。因應問題的變化而改變應對方法,直接而不拐彎。有一天,師徒倆在火車站等車,他提起這一招是他的老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得意「絕學」:一個問題可從多方面作辯證,「一方面」(on one hand)可這樣看,「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又可那樣看,一個問題因而能夠延伸出不同的「問題組」,老師稱為「problematique」。因此,一個問題會如根莖(rhizome)般延伸出很多問題,不會出現單一結論。
直到退休前,李歐梵的辦公室大門總是打開的,任何學生都可以推(敲)門而入,只要你有問題,他總是來者不拒。數年來,每次我約他談論文或聊天,他從來沒有拒絕,有時不想到辦公室,便到德國餐廳喝啤酒、吃香腸,或請我吃自助餐,邊吃邊談。他數次「請」我在他課堂上演講,這是我人生中最榮幸的事,當時我的研究計劃尚未成熟,他亦從未抱怨。他指導我的研究計劃期間從未有用自己的地位施加壓力,只用理據說服我,相處數年,李歐梵從不自誇,有時甚至說要從我身上「學」一些東西,我深感慚愧之餘,也感受到真正的學者風範。如果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們在修行道上,要學的又何止「學術」?
[編輯按:分題為編輯所加]